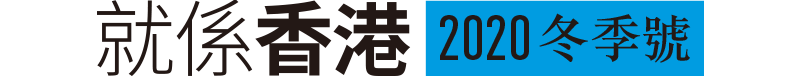Preview//
REtreat//
撰文// 余婉蘭
攝影// 謝浩然
REtreat//
時空歷程,靜修之旅
撰文// 余婉蘭
攝影// 謝浩然

道風 大商場旁有座蓮花聖山
你能感覺,神聖與世俗的距離一再消弭。
或者,從前的道風山,山上山下,還能儼然劃分神聖與世俗的國度,因沙田市鎮尚未膨脹起來、簇擁起來。一切的距離感還是有的。遠眺山還是山,住人的寮屋和田還是低矮,疏落,未填海前,沙田海的岸線還是寬長的,會潮漲潮退。現在樓房起得比山還高還密,整夜車路的聲音傳上山來,行山的熱議的人,來又去。這裡有不少宗教退修場地,然而這裡,四通八達。
排頭村背靠一邊是道風山基督教叢林、神學院,另一頭是佛寺、精舍或別教派的修道場,今日萬佛寺香火鼎盛,成了旅遊地標,一如另一邊的道風山基督教叢林,來的人除了虔誠的教徒,更多是旅客、行山人士或退休的沙田街坊。聽說,排頭村的祖先藍族看中這片土地,背山面海,風水好。七十年代沙田變成新市鎮,排頭村村口對正交通樞紐,又停泊小巴、的士,風水大概一樣保不住了。上道風山的入口,就在沙田火車站出口旁邊,丟空的沙田鄉事委員會向上走,有條小徑,慢的話,要走30分鐘。
我慢慢地行上山—前一晚膝蓋傷了,只得慢行,分外感覺上山的坡度傾斜,滿有一種朝聖的傾斜。向高處行,每一步都有下放的意味。大概因為每走一步也費力,也越快把地面的繁華、雜音和人群,一重一重擺脫在背後。或者它們是被山、叢林,和風所分隔了。
山路指向你能涉足抵埗的聖靈,或叫靈性,假如你有信仰。

若行雲,如流水
到雲水堂登記時,營舍的主任問,你是哪間教會的?我答,嗯,我不是基督徒,我是佛教徒。他一臉好奇,問我,為甚麼上來靜修咁奇怪。我只好答,疫症大部分佛教禪修營地關閉,所以來這了。我好像解釋不到,不得不擺之前交談過的牧師上檯。「我問過某某牧師,道風山應該歡迎不同宗教的人來住宿靜修?」他答:是。然後說:「晚點有個保安,當夜更的,他也是佛教徒。」他不再問。
我查過其他基督教的退修營地,想申請,要列明所屬會堂,牧師簽名作實,道風山是少數向任何人開放。80多年前,最早的雲水堂起在另一邊(即藝術軒和辦公室現址),也是供訪客住宿,掛單多數是佛道僧侶。「雲水」這名字,指居無定所的修道人尋求真正的大師,過程中如行雲流水。雲水也有「行者」的意味,為了尋求覺悟而行走,漫遊。
看道風山的建築風格,佛道、基督教大熔爐,眼可及目的文化共融。好多年前第一次上來,一直就記著這地方。是錯置、變種的古怪印象深刻。它融合兩種的非常不一樣的精神內核,教堂本應神聖、恢宏,中式園林風格則融於自然、恬靜和簡約。這裡聖殿仿照北京天壇而設計,看簷頂是八邊形,簷脊有走獸、道士和尚像;繪瓷作品上,耶穌成了中國古人模樣,分五餅二魚;到處都是漢字對聯和牌匾,而非聖像。
後來和建築歷史學者黎雋維談起,他說,在香港,道風山不是唯一的例子,還有銅鑼灣道聖馬利亞堂,香港仔神聖修院和九龍城聖三一堂。憑常識,會猜得到是為了宗教「在地化」,方便西人在中國傳教而建。「草根階層傳教未必用到文字,好多時要用象徵性的東西吸引他們接觸西方宗教,例如中式建築。」
黎雋維有告訴我另一角度,關於中華文藝復興風潮和政治影響。
「1925年後的建築,特別公共建築,多是傳統中式建築,因為國民黨在孫中山死後,生怕軍閥造反等問題,怕失去繼承中華大同的正當性,為鞏固管治而設計。見例如孫中山的陵墓,風格取自明清時代宮廷,即紫禁城,但內裡西式,現代鋼筋混凝土的結構。後來中國出現好多類似的公共建築,如廣州、南京等,甚至後來國民黨退守的台灣。」六十年代專門為這起個名,叫中華文藝復興風格,他說,一些宗教中式建築,也可統稱為此。



剖開山林,但靜默,不驚動
我去翻一些學術論文(注:黃懿縈的《中國式天主教建築在戰前香港的發展探析》),講到另一個背景,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,中國的知識分子民族意識高漲,開始打擊在華的宗教勢力,促使教會推行基督教的本土化運動。
這種形勢下,教會開始建中式大屋頂,最流行仿清代官式建築風格。
香港也受這些思潮影響。三十年代或更早之前,已出現中西合璧的基督教建築,道風山基督教叢林是唯一由非中國籍傳教士主理。即艾香德,他來自挪威信義會差會。
總覺得,艾香德和其他「在地化」的傳教士不同,他似乎也有過一段「雲水」日子,道風山是他「中國經驗」的總和。最初他1904年到中國傳教,曾跑遍中國的寺廟和隱修場,也去過日本的高野山和神道教寺院等,尋道如雲水,跟好多出家人做「道友」,想皈化他們。
向佛教僧侶傳道、建立交流學習的場所,是他的異象(註:即啟示)。道風山70多年歷史手繪瓷器藝術的出現,為了給還俗的出家人一門手藝,脫離寺廟後,養活自己。艾香德早期一再被指控「顛覆佛教」,「用低劣手段招佛教徒入教。」
香港建立的道風山道場,其原型來自艾香德在中國南京成立的景風山,即他所推崇唐朝時傳入中國的波斯景教。因為1927年南京暴動,景風山受到破壞,他只得把修道場遷離中國,在東南亞四處尋找新地方,最後他選了香港。
為甚麼是香港?又為甚麼在沙田落腳?
到底因為近中國。沙田當時可以從吐露港走水路,或者經九廣鐵路的火車方便來往中國。
道風山道場在1931年成立,沒多久,艾香德定期到中國旅行,西藏邊境、峨嵋山,五台山還有道教名山華山等,也去了東南亞佛教國家,如印度、緬甸等,為了傳福音和招人來道風山。

第一晚入住,連同我,只有三個住客,疫症關係,平日來學習和住宿的外國教徒和中國大陸教徒都沒來。我沒吃晚餐,倒吃掉一包山楂乾,因買完才擔心山楂乾帶上山惹蟻,想趕快吃掉它;第二晚的晚餐,炒蛋鹹而菜煮老了,白飯任裝,是廚師五點放工前先煮定保溫。是的,山上只剩下數人和他們的晚餐。瘦小的女人吃晚飯前,叫我夜晚不要走太遠。野豬、蛇和馬騮夜間出沒,留在室內較好。
聽了我就沒有走太遠,只走出雲水堂的石屎階梯,向沙田新城市廣場方向張望,市中心的光竟讓人覺得閃耀而靜止──回到五十年代,下面當時應還是舊墟那昏暗模樣。
一列火車滑過黑夜,一道輕巧匍匐的光,或像城市規律流動的血管。日間比較不能察覺,儘管班次頻繁,因地面過於繁忙,人造的萬物多彩,也同樣繁忙運作,輕易忽略了正行駛中,日夜穿梭的九廣列車。
那時,艾香德在這邊張望下去,俯視沙田峽谷,記憶唯一不變,鄉村山野間能記認的,同樣是那列火車在穿梭嗎?1910年九廣鐵路通車,穿過沙田段的煙墩山隧道,就是沙田谷了。那列行駛的火車從蒸汽,至柴油,後來成了雙軌電氣化列車。那種劃過的方式,似曾相識。是從道風山上,張望山下,所能見證到時間的軌跡,一直是向前,不回頭。
在叢林內通向「道風大千」那條小徑,有一幅道風山彩繪全景圖,留存鳥瞰下,魚米之鄉之貌:大埔道是唯一貫通的汽車道路,瀝源等小村落依淺河而建,鬱蔥而古香──畫中那條已建設的火車路軌,剖開山林,但靜默,不驚動。因火車尚未駛進。


覺悟是,放下是為了背負
1930年,這座山頭盛惠3,705墨西哥金幣,引針山的自來水,動用超過100個工人開鑿和建造,不少粗工還是客家婦女擔當。精通中國佛教健築的丹麥建築師艾術華設計和構思。艾香德最早看中這座山,也為了延續和佛教徒的聯繫,附近寺院道場林立,如最早的佛寺道榮園、西林寺和道場紫霞精舍等。萬佛寺的創辦人月溪和尚,曾在1933年到訪道風山,他用英文留過字。
所以這裡的宗教符號,是十字架出自蓮花而生。艾香德他們早期在叢林的生活規律,和出家人無異,日常飲食都是素食。做禮拜,授課,默禱,懺悔,踐行和談話都有固定模式,還有靜坐,明顯是佛道文化的傳統。艾香德最早的夢想,建立可以媲美佛教寺廟道場的基督教隱修院。
若用「隱修院」而非「教堂」來看待道風山叢林,亦即尋求覺悟的聖地,那你的世界觀變成另一種。劉牧師有說,道風山不少設計和空間,供個人或團體,靜修默想之用。例如明陣。本是公元七、八世紀基督宗教建築的元素,有點像迷宮,迂迴曲折,但有清晰指向的路徑走向中心,入口也是出口,以前刻在建築物,讓教徒以手指頭代足,在明陣「走」一圈,安靜心靈再參加聚會。其後也有一些傳統,朝聖後走明陣,作為旅程的結束。
道風山的明陣設於另一個捷徑出口(出口也是入口)。劉牧師說,明陣是很好的靜修工具,與神一起「步行」,尋求指引。
還有蓮花洞靜室,建在聖殿的地下,用來作苦行,苦修和精神重生。劉牧師說,進入蓮花洞前,先在黑暗狹小的懺悔室默想,先卸下一點,再步入另一個洞穴,見「放下重擔」四字──暗室中,只有自己(基督徒則覺得自己以外,還有神同在)—離開時,轉身卻見:「背起十架」。暗示這從來不是一種與世隔絕,只求隱逸,孤絕的修行。基督式的覺悟是,放下是為了背負。據說是艾香德構思蓮花洞,他自己早晚都要入洞一次,每次半小時,叫人不要打擾他,晚年猶甚。他深愛靜坐,求取心靈之安息,形容經驗「好比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開悟。

尋道,就是讓真理和你說話
剛完成幾天靜修的女基督徒,離開前,有問,佛教有沒有「道」這概念?我只想到道教的「道可道,非常道」,或儒家的天道。我說,字眼上好似少用。
她說,道即是由上帝行出來的道。道即是神。
道風山的聖殿掛有「道成肉身」的牌匾,更早之前有一塊,和南京景風山叢林一樣,牌匾是「太初有道」,出自同一章聖經《約翰福音》。而道風山的「道風」,是基督的聖靈,意思隨風吹。風是給予生命的風。聽說,中國佛教領袖太虛和尚,曾對他的老朋友艾香德說,然而,道也可以在我們之中成肉身。
這是本質上佛道和基督信仰的分野。這裡幾天,有位基督徒婆婆急著想向我傳教,說神的旨意叫我們相遇。我疑惑,兩者微妙的相近與不同,結果第一日入蓮花洞默想時,無法專心,因眼前是耶穌釘十字架像,它要你相信恩典。終究是我看不到琉璃窗後,潔淨的光透進來,風在擺動葉子沙沙,雲易變。
直至差不多離開道風山,才遇到傳聞中的佛教徒保安,我問他,昨晚見到的花貓,是否道風山養,他說,是啊,隻貓很肥,因為好食好住。保安高瘦唇薄,樣子很理性,和劉牧師、來靜修的教徒,氣質上的感性溫馴,輕聲細語很不同。教徒的靈性所屬,大概外貌可窺一二吧?
佛教徒保安每早八點半,跟基督徒在聖殿早禱,連玫瑰經、聖詩他瑯瑯上口,然後工作。「早禱其實更像一天開始的儀式,讓自己有更平靜、喜樂的心迎接新一日。」
因宗教的本質都一樣,追求世界的真理,導人向善。聽見我的疑惑,他說自已將教堂當佛廟般,照常生活、修行和工作。「基督教說的聖光,其實和佛光沒有分別。」

也不過一兩天,一聽見敲鐘聲,早禱、團契就聚來人群,聖殿還舉行了年長教徒的喪禮禱告和儀式。下午來了一群活潑,戴漁民竹帽的中學生參觀。傍晚一班詩歌團體來練習。
聖詩聽來沒有白天的莊嚴,入夜,歌聲變得很像風鈴。
讀艾香德的童年回憶,他在人跡罕至的小山和森林中度過,和沈思,其中的教堂山,構成他「猶太聖山」的雛形:「那是他家的附近的圓頂形小山,他可以從這小山見到大海,島嶼,沿著峽谷有教堂和白色房子。」艾香德最早在大自然而非教堂,感受最無以言表、被捉緊的宗教感。
離開中國的名山大岳,來到巴掌般小的香港,他建立自己信仰的聖山。
晚飯前,瘦小的女基督徒說,十多年來,她固定上來道風山,安靜幾天,因人需要一人梳理,一人思考,一人靜默。這次上來,因為小兒子被控暴動罪,她搬來一堆法律文件和書籍,預備為自己身為母親作答辯用。她需要靜。事實上這幾天,或者大部分時間,我在山上無聊滑手機,見到多數都是暴動上庭新聞,和讀了一篇分析「梁天琦在一場無領袖的運動中,如何作為領袖」的專題報導,之類之類。
瘦小女人領我去她平時靜默的地方,面朝山林,青蔥廻然叢生,建築物被隱埋其中。「尋道,就是讓真理和你說話。」她說,靜的意思,你見各種層次的綠裡,有枯萎有抽新芽的,能看很久。大概這是靜的意思。
10月某天三號風球,風吹得呼呼。向東的巨大十字架,抬頭就是「成了」。有教徒祈禱,讀經和唱聖詩,他們先走一段傾斜的山路上來。清晨,習慣站在聖石旁晨運的阿伯說,每天清晨六點幾,他都見到同一個女人,拿著花,搭的士上來祈禱、唱詩,然後放下花。「好神心,日日如是。」也有個沙田站的港鐵職員,日日中午一放飯,走上山,跪著抱著十字架,低聲和神說話。從沒有人知道他說甚麼。

一些舊時紀錄片,差不多90年前,風也一樣吹著山野。那時出家人、喇嘛或居士、基督徒也是圍坐在同一座道風山山頭上,聽道、講經和默想。
他們一樣如此提煉「靜」:上山,默禱,下山。通向十字架的,從來只有一人身窄的門。我想,風、氣氛中總有著信仰默想的能量迴蕩,讓今日山界已模糊難分的道風山,仍保有向內的神聖。想起向我傳教的婆婆,坐在一堆年月佇立的石頭堆中,祈禱的姿勢也像石。
︎更多內容:《就係香港》2020冬季號專頁
Let’s Read HK Together,按此立刻訂購!
Let’s Read HK Together,按此立刻訂購!